
《上帝一直在搬家》:走出殖民、與窮人為伍,拉美解放神學如何發展?
by 精選書摘|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解放神學以不同的形式鼓勵信徒投身政治鬥爭,清楚表明教會不再是站在壓迫者一邊。這個運動在一些高壓社會帶來了實質的政治後果,而天主教的激進派甚至始終與馬克思主義團體保持活潑對話。 |
文:菲立浦・詹金斯(Philip Jenkins)
南方基督宗教
「以主之名,以那些哭聲震天的受苦難者之名,我央求你,我命令你:停止暴行。」
——薩爾瓦多大主教羅梅羅(Oscar Romero)
我們可以對南方基督宗教的信仰與實踐作出若干預測,但上帝與世界未來的關係又會是怎樣呢?在深受啟蒙運動影響的西方人的想法裡,基督宗教未來最大的轉變應該是單獨成為生活的一部分,與日常生活無涉。在這種西方式的觀點裡,靈性生活主要屬於私領域,只與個人的心靈有關。特別是在美國,人們普遍相信教會與國家、神聖與世俗的領域應該像油與水,完全脫離開。不過,這種二分法卻是西方歷史大部分時期都不存在的,甚至是人們無法理解的。歷史學者指出,在中世紀的歐洲,任何在「宗教」與日常生活之間畫一條界線的嘗試都會受到嚴厲譴責,也沒有中世紀的歐洲人能夠明白教會與國家這種現代的二分法。
就此而言,「全球南方」的許多社會要更靠近中世紀的歐洲,而非現在的西方。近幾十年來,非洲、拉丁美洲、亞洲許多地區的政治局勢,都深受教會中人態度的影響,神職人員一再站在政治舞台的中央。這種現象在現代西方不是未曾發生的,如金恩博士和朋霍費爾(Dietrich Bonhoeffer;譯註:德國基督宗教神學家,因為反納粹而被處死)就是代表性的例子,只不過這類人的出現頻率要遠低於南方。南方的基督徒社群裡,樞機主教和主教往往是全國性的精神領袖,而類似的情形自17世紀以後就沒有在西方發生過。一如中世紀的歐洲那樣,南方神職人員對政治的干預具有明確的宗教泛音,他們會援引古代的先知傳統和透過對《聖經》的重新解釋,佐證自己的政治立場。由此可知,並不是只有伊斯蘭世界才會利用宗教的意識形態來爭取政治上的效忠者。
儘管不容易想像,但在50年後,不只基督信仰會在第三世界繁榮昌盛,基督信仰的政治力量也會如此。既然接下來幾十年基督徒人口與文化影響力勢必大增,我們就有理由去問,這種信仰是否也將為世界大部分地區提供主導的政治意識形態。我們甚至可以想像會有新一波基督宗教國家出現,它們的政治事務是與宗教事務緊密聯結在一起的。如果真的是這樣,南方很快就需要面對一些傳統基督信仰中心爭論已久的問題,諸如政教關係的問題和敵對教會的法律地位的問題。其他在這種環境下無可避免會出現的問題還包括寬容與多樣性的問題、少數宗教社群與多數宗教社群的關係的問題,以及應不應該用宗教性的法律來規範個人道德或行為的問題。不管這些問題是以什麼方式解決,南方教會的政治向度都一定會進一步拉大北方與南方之間——也就是世俗化社會與宗教化社會之間——的巨大文化鴻溝。
走出殖民
在全球南方,教會與國家攜手同行的歷史為時久遠。在殖民統治時期,教會享有國家的扶助,而它們則用強烈的政治保守立場來回報國家。這時期的教會,事實上是政府的武器。在拉丁美洲,天主教會的獨尊地位一直持續到各國獨立以後許久,在一些國家甚至持續到現在。以智利為例,要晚至2000年,政府才立法廢除了天主教會在文化和教育領域的法定霸權,哪怕該國的新教只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一個少數派。此前,只有天主教徒才能被任命為軍中的神父,也只有天主教的組織才享有財產稅和捐贈稅的豁免,而學校裡的宗教課程教的清一色是天主教的教義。在20世紀初,天主教的思想家曾引入過「整體論」(integralism)的觀念,這是一個中世紀天主教觀念的翻版,主張天主教的社會思想應該應用到國家包括社會、經濟和政治在內的每一方面,換言之是主張神職人員在世俗事務上發揮廣泛的影響力。後來,這個主張雖然因為與極右思想和狂熱反共主義靠攏而受到摒斥,但仍繼續存活在檯面下。
在拉丁美洲的政治衝突中,天主教一向都站在統治階層那邊,甚至達到贊成鎮壓的程度。在1970與80年代的阿根廷危機期間,天主教會因為默許當局的暴力而臭名遠播。站在衝突另一邊的往往是些強烈反對天主教的激進派。在墨西哥,天主教會於20世紀前半期激進派當權時曾受到激烈的迫害。非洲的情形也一樣,曾經受殖民當局扶持的傳教士教會在群眾起義期間一再受到攻擊。
然而,自20世紀開始,第三世界教會認同改革大業甚至革命大業的情況卻愈來愈多。儘管教會的意識形態傾向變得與以前大大不同,但一個傳統的觀念仍然繼續發揮作用:教會應該全面介入政治,甚至領導國家。20世紀初,政治立場激進的教會主要都是從傳教士教會分離出來的,其領導者多是奇倫布韋和哈里斯一類的非洲先知,或者像巴西傳奇的西塞羅神父(Father Cicero)一類極端派天主教教士。然而,自50年代開始,同樣的觀點滲透到了包括歐洲、北美和第三世界在內的主流教會。新教信徒對於該教會未能奮起抵制納粹德國的記憶猶新,為了補贖前愆,推動反種族主義與反南非隔離政策的運動不遺餘力。這些觀念也在世界基督教協進會裡找到一個要塞。自1970年起,該會開始幫助一些激進和左翼的政治運動。然而,對於該會應該支持反對不義國家至何種程度,卻引發了激烈的內部爭論。爭論在1970年代白熱化,當時世界基督教協進會定期用該會的特別基金,資助反羅德西亞白人政權的游擊隊。在批判者看來,這樣的資助是過頭的做法,讓該會從積極份子一變而為好戰份子。
在羅馬天主教,自第二次梵蒂岡會議(1963至65年)之後,各種解放神學就廣為盛行。至少有一段時間,教廷不只容許激進的政治行動,甚至為之背書。1967年,教宗在其通諭《民族發展》(Populorum Progressio)中呼籲教徒應該「大膽轉化」全球財富分配不公的現象。天主教和主流的新教教會都分享相同的觀念,認為教會反對高壓的政權,既是權利也是義務,認為教會應該為改變種族與經濟的不公義而戰。兩者的政治積極主義在基督宗教的歷史上都有豐富的先例可援。他們視〈出埃及記〉(〈出谷紀〉)為一部奴隸的解放史,又以阿摩斯(Amos)一類的《舊約》先知為執行正義的榜樣。同樣地,在《新約》裡,解放神學派也找到豐富的彈藥,可供進行激進的社會批判之用。其中一個觀念是「時辰」(Kairos),意指上帝終將審判人類的不公義和剝削性的社會結構。
解放神學以不同的形式鼓勵信徒投身政治鬥爭,清楚表明教會不再是站在壓迫者一邊。這個運動在一些高壓社會帶來了實質的政治後果,而這是因為神職人員要比一般人有較大的行動與發言自由。如果一個一般工會會員說出反壓迫或反酷刑的話,他很可能會入獄或殺害,換成是一個教士說出同樣的話,當局的表現會節制許多。把一個教士(特別是天主教的教士)下獄,是會招來西方媒體的譴責的,而且會有與梵蒂岡發生衝突之虞。於是,神職人員成為了反對運動的發言人。如果一些抗議或聚會是在教會的主導下進行,當局也會表現出類似的節制。
教會提供了某種的安全地帶,而激進派的教士也把「避難所」這個中世紀的基督宗教觀念重新闡釋、運用。1973年智利軍事政變的血腥餘波中,被迫害者的家屬求救無門,唯一顯著例外是受天主教保護的組織「團結代管協會」(Vicaría de la Solidaridad;譯註:聖地牙哥樞機主教席爾瓦於1976年成立,是一個協助受政治迫害者、酷刑受難者、失蹤者及其家屬的重要組織)。在1970年代的巴西,最有力的一個反對陣營就是由聖保羅大主教阿恩斯(Paolo Arns)領導的天主教會:他盡情地利用軍事獨裁者不敢碰他這樣地位宗教人物的自由。
當然,教會的免疫力是有局限性的,只會在其所在國的政府在乎世界的意見時才會發生作用。例如,「避難所」的原則雖然在威權主義的南韓行得通(這是因為南韓與西方關係密切),在孤立和偏執的北韓就行不通。即使是北半球,一些受到垮台威脅的政府還是會對教會作出反擊。正因如此,大主教羅梅羅 (Oscar Romero)才會仍不免一死:1980年,他因為挺身正面對抗薩爾瓦多的極右政權而遇害。1989年,另有六個耶穌會教士在該國持續的血腥鎮壓中被殺害。瓜地馬拉的情形也類似:1998年,一個身兼教區人權辦公室主任的輔理主教遭到殺害。不過,這種現象反而讓教會的威望更加提高,被視為受剝削者的保護者。在20世紀的最後25年,很多國家的教會都因為勇於反抗高壓的政權而獲得了讓人艷羨的聲望。

拉丁美洲與解放運動
解放神學在不同地區的發展方向相當不同。解放神學觀念最初開花結果的地方是拉丁美洲,但在某些方面,它的影響卻不如其他地方長遠。自1960年代以迄80年代,天主教激進主義與拉丁美洲的歷史都密不可分,因此,想要在這裡鉅細靡遺地介紹,幾乎是不可能的。
天主教的政治積極主義在1968年催生出某種憲章般的東西,當時,拉丁美洲的主教在哥倫比亞的麥德林(Medellín)舉行會議,會後發表了一份形同「美國獨立宣言」的文件。這篇宣言大量借用馬克思主義的語彙,譴責新殖民主義、富國對貧國的剝削、資本主義的制度性暴力,又呼籲各國進行根本性的經濟與社會改革。1971年,祕魯神學家古提雷茲(Gustavo Gutiérrez)出版了《解放神學》(Teologia de la Liberación)一書。接下來20年,很多拉丁美洲的教會領導人都極看重「優先選擇與窮人為伍」(preferential option for the poor)的呼籲。天主教激進主義的其中一個代表人物是卡馬拉(Helder Cámara),他在1964至1985年間擔任巴西累西腓(Recife)和奧林達(Olinda)兩省的大主教,被稱為「貧窮者的主教」。卡馬拉神父也是位整體論者,這反映出,左翼思想與這個古老的神權政治觀念有多相容。天主教的激進派透過發展「基要社群」(base communities)而獲得相當多的群眾擁護,有些分析家曾認為,它們將是未來人民教會的原子。這些組織採一種鬆散的列寧主義模式,有如新社會的種子般寄生在舊社會的外殼中,只等成長茁壯,就會把舊的殼丟棄。在1970年代晚期,據說單是巴西一地,就有八萬個這種基要社群。
天主教的激進派始終與馬克思主義團體保持活潑對話,有一些天主教教士甚至加入了革命的行列。早在1960年代中期,那些在窮人之間工作的教士就開始變得具有強烈的政治傾向,有一些甚至全心期待革命的到來。其中一個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哥倫比亞的教士托里斯(Camilo Torres),他一直與一支左翼游擊隊並肩作戰,後於1966年在一場戰鬥中被政府軍殺害,成為極左派的國際烈士。他不介意與左翼結盟,因為「甚至連共產黨自己也不知道,你們中間有很多人都是信實的基督徒。」在托里斯看來,「革命是取得政權的方法,而只有取得了政權,才能餵飽窮人,讓不蔽體的人有衣服穿,教導文盲,實現仁慈和愛人如己的理念。因此,對基督徒來說,革命不但是被允許的,而且是責任,是唯一可以有效而完整達到愛所有人的方法。」
解放主義者的希望在1970年代晚期到達一個新高點。桑定游擊隊在1979年成功推翻尼加拉瓜政權,好些前任和現任的教士都被延攬到政府裡去。翌年,羅梅羅大主教的遇刺創造了一個話題,也使中美洲成了全世界左翼基督徒的焦點。不過,後來的歷史發展顯示出,這些事件已是解放運動的強弩之末。1978年,若望.保祿二世當選為新教宗,而這位波蘭出身的教宗對任何形式的馬克思主義都深感不信任。貫穿整個1980年代,梵蒂岡的新領導階層都致力於系統化地讓激進派的神學家消音,其中包括巴西的岡博夫(Leonardo Boff)。與此同時,中美洲的革命前景也因為大環境的改變(包括美國的介入和蘇聯的解體)而破滅。桑定政權也在1990年下台。
接下來20年,一系列新的主教人事任命讓拉丁美洲天主教會走入了一個保守得多的階段。新作風的一個代表性例子是祕魯主教西普尼亞里(Juan Luis Cipriani),他是祕魯阿亞庫喬(Ayacucho)教區的主教,也是性格高度保守的天主教組織「主業會」(Opus Dei)的一員。他的位子特別具敏感性,因為阿亞庫喬正是毛派游擊隊「光明之路」(Shining Path)的風暴中心,整個1990年代,「光明之路」游擊隊都受到政府軍的血腥鎮壓。西普尼亞里選擇站在政府這邊(這也是梵蒂岡的立場),力陳祕魯的政權是正在為基督宗教和文明而戰的。他反覆為政府軍的殘暴行為辯護,主張「大部分的人權組織不過是政治運動的,成員幾乎都是馬克思主義者或毛澤東主義者。」儘管立場偏頗,西普尼亞里還是在2001年被提升到樞機主教的地位。
在這樣的領導下,那些在前一代教會領導人的澆灌下欣欣向榮的大眾組織走進了政治冰河時期。很多「基要社群」都枯萎了,無法充當激進天主教改革運動的原子,只有少部分生存下來。很多當初懷著改革理想而進入天主教的人都改投到五旬節派,因此,五旬節派的勃興,部分可說是天主教無法兌現早期的革命憧憬的結果;在好些拉丁美洲國家,五旬節派發展得最快的時期,都是1980年代政治鎮壓大行其道之際。
與1970年代過度樂觀的希望相左,拉丁美洲並沒有成為被左翼神權政治統治的地方。儘管如此,如果把近期的轉變視為拉丁美洲天主教會完全拋棄理想主義的表現,則是不確的。雖然該地區有向右轉的趨勢,但天主教神職人員仍然是重要的政治角色,常常站在民主與人權這邊。其中一個與西普尼亞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宏都拉斯的羅德里格斯(Oscar Andrés Rodriguez Maradiaga),他是特古西加爾巴(Tegucigalpa)教區的主教,與西普尼亞里一樣,都在2001年被拔擢為樞機主教。儘管顯然不是梵蒂岡所樂見的,羅德里格斯仍然放言高論社會正義的議題,而且成為促使取消第三世界債務運動的主要發言人之一。在宏都拉斯國內,他鼓吹政治民主不遺餘力,為了表揚他的功勞,國會甚至有點誇張地選舉他為新任的警察總監。雖然羅氏婉拒了,但這個插曲可以反映出,教會並未完全棄守它在世俗生活中的恰當位置。
相關書摘 ▶《上帝一直在搬家》導讀:「全球南方」將會是下一個基督王國?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上帝一直在搬家》,立緒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聯合勸募。
作者:菲立浦・詹金斯(Philip Jenkins)
譯者:梁永安
基督宗教已經處於瀕死?伊斯蘭教才是宗教的明日之星?宗教戰爭又將歷史重演?基督宗教大變局正在進行。
本書是任何對基督宗教和全球大趨勢感興趣者的必讀之作,針對基督教人口的增加、遷移以及其與伊斯蘭教關係做了深入的研究分析,探討全球宗教史上驚天動地的大變動——基督宗教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爆炸性擴張,以及它可能帶來宗教、政治、社會與文化的大影響。
作者詹金斯質疑當代社會與世界觀察家杭廷頓,固然正確預見了穆斯林將會人丁興旺,卻沒有看出基督徒也會出現人口爆炸現象。並進一步指出,「宗教認同感」將為全球政治面貌帶來重大影響。目前政治鬥爭的前鋒並不是階級,而是對上帝持不同見解的人,且大規模的宗教衝突與競爭業已在進行中。
在這部鮮明、有挑釁性而研究詳盡的作品裡,詹金斯得到的結論是︰基督宗教正在崛起中,而且是以更傳統的面貌展現。想要全面了解這個現象的意義,就不能不對今日的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有所了解。本書是任何對基督宗教和全球大趨勢感興趣者的必讀之作。
- 原書名:《下一個基督王國》
- 隨書附贈《自己拯救自己》一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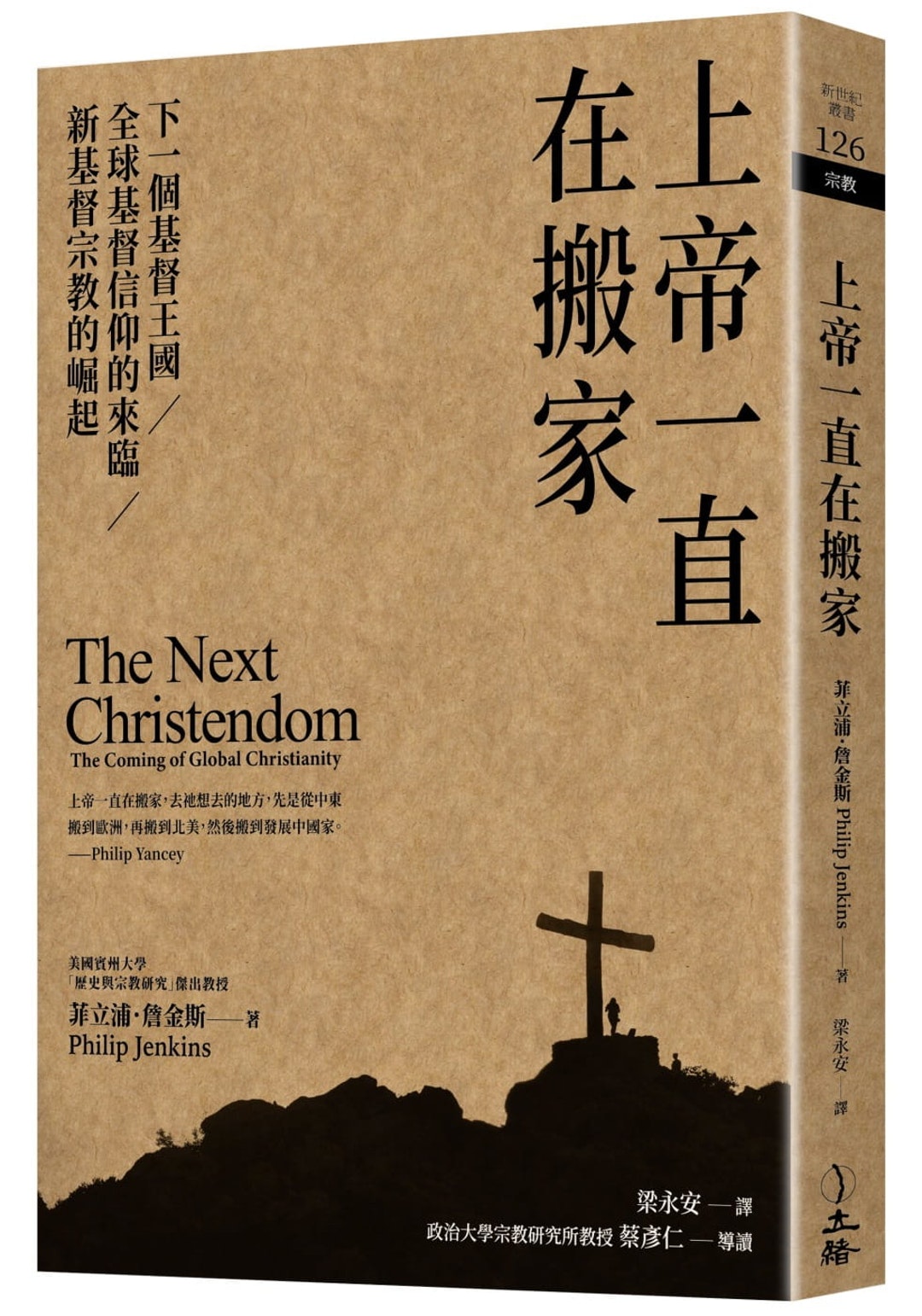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